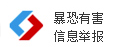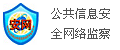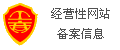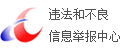|
宿夜花 1996年的澳大利亚电影《闪亮的风采》提名了多项奥斯卡奖,更是让只有不到一半的戏份的杰弗里·拉什拿下最佳男主角,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奥斯卡影帝。电影以一种新颖的方式与角度,侧重展现钢琴奇才大卫·赫夫高特(David Helfgott,下文简称赫夫高特)的特殊性格心理与家庭文化环境、父亲教育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展现主人公对自由理想与艺术生命追求过程中的动人故事。 《闪亮的风采》作为音乐传记片本身,它为观众欣赏古典乐、认知并了解钢琴奇才赫夫高特、反思家庭关系人生价值提供了一个优秀范本。 
“奏鸣曲式”结构与“水”的意象将音乐结构成功移植到电影之中,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秋日奏鸣曲》无疑是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典型,剧本的情节起伏、叙事的节奏快慢疾缓有着类似“奏鸣曲式”的结构: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在这种独特的结构之下,伯格曼仍旧是以钢琴家母亲为视点、探讨家庭关系、情感心理、精神信仰等一贯的母题。 
斯科特·希克斯执导的《闪亮的风采》除却在结构上有着类似方式的移植之外,古典乐及相关元素还承担着叙事与表意的重要功能。尤其是贯穿全片的20世纪知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简称拉三),一方面是通过拉赫玛尼诺夫与影片主人公赫夫高特人生经历上的相似性来完成一种隐性互动;而更为重要的是:难度颇大、对生活阅历情感经历要求颇高的拉三,既是父亲精神施压与强迫意志的象征,又是赫夫高特挣扎与精神成长、救赎与自我寻找的写照。 作为一部注重娱乐性与观赏性、在人物事件的真实性与创作的艺术性上均有追求的影片,自然不会像伯格曼的电影将哲学性思考作为最高目的,而是通过层层剥茧般的故事、富有表现力的画面,一步步地揭开人物的形象和心路历程。 
这种结构尚且对缺乏相关知识的观众而言稍显晦涩,影片通过“水”的意象及其变体作为串起全片段落的情感暗线。水作为洁净之物,洗刷污浊、去伪存真,见了本性与真心;暗夜冷雨中狂奔的动作,寓意着赫夫高特开始摆脱世俗喧嚣、在沉静中追寻自我;浴室中的水花像父亲喷薄着的暴力,成了一种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对“水”的感悟。而从雨水、浴室、游泳池到大海,“水”形式在不断地拓展;水光旖旎,赫夫高特正是通过不停地净化心灵、遗忘伤痛、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中获得一种沉浸于艺术中的单纯快乐。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父子关系 从剧作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的角度看,影片极为突出的一点在于,对赫夫高特的家庭文化、成长环境、父母的教育方式刻画的极为细致,这为使得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解读人物提供了严密的逻辑。除此以外,影片并没有为了凸显性格心理而淡化复杂、严酷的现实背景:二战伤痛、美苏冷战,这些奠定20世纪全球格局的历史事件,对这个从波兰逃离到澳大利亚的犹太家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影片对主人公童年、青年的展示部分甚至多过成年,由此可见,性格的成因与家庭文化、宏大历史的渊源,是影片所致力于呈现的东西。父亲彼得的形象是一种双重象征,既是历史意志、父辈意志对个人的异化,也是传统家庭教育观的代表。 
作为出身在波兰的犹太人,父亲彼得自幼目睹法西斯的暴行、逃离杀戮、流离辗转到了澳大利亚,因而他对法西斯暴行发自内心的痛恨、对昔日家族的眷恋与对当下家庭的珍视,有了严密的历史依据。爱好音乐的父亲因为小提琴被父亲砸毁,则将这种理想的遗憾转嫁到主人公赫夫高特身上,因此他对儿子近乎偏执的教育正是他在时代洪流与父辈意志强迫下双重创伤的宣泄。 
影片恰恰是将这种代际间的意志传承提炼出了一种普世性的模式,即是父辈在遭受来自历史不可抗力的悲剧命运与上一代的意志强迫之时,无形中将这种悲剧用同样的“暴力”形式转嫁到子辈身上。法西斯的暴行导致了他的创伤,他就用冷漠与敌视的“冷暴力”对待其他人,封闭了家庭与外界的交流;父亲践踏了他的音乐梦,他就将他未能实现的梦想强压到儿子的身上。这种往复不断的心灵压制、意志强迫导致了一个又一个被异化的人。 
传统教育观念中的“忠诚于家庭”、“孝顺父母”在父亲的偏执与狭隘的心理操纵下,形成了一种对主人公病态的控制欲,不但千方百计阻挠主人公去美国、英国进修,甚至造成了主人公的精神病与自闭性格。这与东方家庭中普遍存在的保守、封闭、陈旧的教育观如出一辙,在王小帅的《青红》中,姚安濂饰演的父亲的失语与苦闷转嫁成对高圆圆饰演的青红的另一种“禁锢”。天才的精神救赎与自我实现 影片大量的父子关系的刻画是为了阐释主人公赫夫高特的性格成因,他的沟通障碍、自闭心理、精神紧张症使得他忍受着异于常人的痛苦与挣扎,他心中对音乐的狂热对理想的追逐并未随着父亲对他狭隘的占有欲与控制欲而停止。 
与作家凯瑟琳的忘年交是他生命中的一段重要情谊,而他们作为精神之友,关系也超越了世俗定义中的寻常关系。凯瑟琳的包容与睿智、对他个性的尊重与爱使得他感受到亲情异化后的“父权”家庭感受不到的温暖。教给赫夫高特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忠于本性与内心的自由灵魂。在她的鼓舞勉励下,赫夫高特开始反叛父亲的意志、挑战父亲的权威,离开家庭赴英国学习音乐。 
而自信独立的职业女性吉莉安给了他爱情、并成为了他的妻子。在爱与自由的救赎之下,他重新焕发出光彩与活力,迸发出的天真浪漫、宛若孩童般的诚挚与稚气,逐渐摆脱父亲家长权威意志下的恐惧与压抑。影片中女性角色对天才主角的精神救赎意义,与后来罗素·克劳主演的讲述数学家纳什的《美丽心灵》形成一种对照。 
杰弗里·拉什仅仅凭借不到一半的戏份拿到了第69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从电影一开场他用精心设计的奇腔怪调展现出角色癫狂与神经质,痴言嗔语、重复絮叨一些不知所云的话,一个常人眼中性格孤僻、性情乖戾的“奇人”形象便立住了脚。而本片中的钢琴弹奏均由演员本人亲自完成,尤其用一曲《野蜂飞舞》展现出赫夫高特由潦倒颓靡重新走向振奋的欢欣雀跃,酣畅淋漓。 
无论是《加勒比海盗》中城府颇深却不失诙谐的巴博萨船长,还是《国王的演讲》里乖戾却讲原则、包容又睿智的治疗师罗格,主流商业电影中的杰弗里·拉什,既有着对角色的通俗表现力,又不会囿于一种脸谱化的模式与套路。因此,他塑造出的人物既鲜活又生动,那种深刻与复杂蕴含在表演的琐碎细节中,这其中无不彰显着他对角色整体的理性建构能力与外部细节表现上的技术功底。理性的光芒:爱与自由之歌 导演斯科特·希克斯说:“这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实现了我们所有人的愿望,那就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一起分享人生、爱情和音乐的伴侣。” 
回到影片的片名“Shine”,中文译名“闪亮的风采”还是颇得精髓,如果进一步去叩问:闪亮的究竟是指什么?正如影片的结尾所言“万物总有季节,永远不会消失,我们只需要把握季节变幻”。影片中的父亲以爱之名对个体个性的异化、对生命天性的禁锢,真正使得赫夫高特获得精神自由与完成自我价值的是一种包容的爱、生命的自由,一种忠于内心、释放天性的理性精神。而父亲逝世后,父子间的隔阂与矛盾也因此消解,这种包容与和解也是影片所蕴含的道理。 
如果说在稍早两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沙漠妖姬》获得的最佳服装奖让“澳洲元素”(澳洲电影、影人及泛澳洲文化元素)开始广为世界瞩目。随着《闪亮的风采》击败汤姆·克鲁斯等好莱坞当红大明星夺得影帝,凯特·布兰切特、罗素·克劳几年后的相继获奖,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地区的电影人及文化元素成为好莱坞体系下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而《魔戒》(即《指环王》)的全球性轰动即是这种文化通过电影媒介最成功的一次输出。而放在世界电影的大语境下,影片的创作价值取向恰恰也是90年代文化环境的一种反映。在90年代的同期,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李安的《饮食男女》等华语电影亦有提名最佳外语片等奖项,它们所探讨的主题也多是现代价值观对传统观念的解构与重塑、自我的精神迷失与追寻价值认同。由此可见,不同语言的电影内部的文化反思在一种全球化的视角下有了一种相似性,即是对电影本体意义的深化与生命意义的永恒拷问。 ? 本文版权归 宿夜花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网站首页 > 娱乐 > 正文
网站首页 > 娱乐 > 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