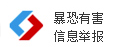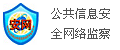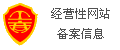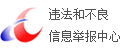|
写生,是画者摹写、感悟、升华自然与自我的方法与手段,是在自然中探寻创作灵感,发现新的绘画形式语言,找到新的表现内容、方法的有效途径。在对自然的品味与感悟中,写生能使画者胸襟开阔、想象丰富、创造不竭,从而达到精神升华、灵魂净化、生命提升的境地,在主客体之间搭起桥梁甚至无缝对接。因此,厘清并掌握古今山水画的写生模式是极其必要的。 
一 写“貌”、写“形” 写“貌”,也就是得其“形”,是画家搜集素材、准确把握物象精神的必要途径,这是基础,也是前提。因此写生时,既要把握整个山水的格局、气势、精神,更要掌握其得以形成的微观元素,比如处于不同节令、地域物象的形态、体貌、高低、穿插、质感等要素,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时而异”,而非依靠习得性心理定式、方法和绘画语言去观察、处理事物,否则最终落个“天下山河一大统”的后果。因此,观察自然时,必须做到整体与局部的有机统一,既要“远望之以取其势”,又要“近看之以取其质”。就特定地域环境下的山石、树木、云水、流瀑也要观察细致入微,以符合自然规律。 山水追求的终极目的是“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的“胸中丘壑”,但写貌仍然是山水画家写生的必要模式之一。元代画家黄公望云游时就“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摹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写形写貌也需要对物象进行选择、取舍、提炼与概括,它不是山水画家的终极目的,却是艺术家提升艺术水准和独特艺术风貌的必经之路。 
二 写“真”、写“神” 五代画家荆浩提出了“图真”的概念,“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只得到物象之表而得不到物体的内在生命精神,就没有得到物象之“真”,也就没有得到物象之“气”。山水画追求的不是对客观自然的模拟,而是透过自然表象去捕捉、传递事物的本质与生命。在追求“真”的过程中,不但不反对“貌”或“形似”,而且是将其作为获取“真”的必然过程和手段。换言之,“写貌”是“写真”的前提和基础。荆浩写松之“真”是建立在对松之势、之气、之格的千察百悟和“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的心血之上的,绝非仅移形模貌所能奏效。 写“神”,就是要把握物象的精神实质。元代“‘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噫!此大痴之笔,所以沉郁变化,几与造化争神奇哉”,与大自然朝夕相处,达到物我相合的地步,主客观达到了高度统一,以至于“意态忽忽”。在这种状态下,画家的写生是建立在“技”之上的“道”的传达,遗貌取神。明代李日华曾写道:“每行荒江断岸,遇欹树裂石,转侧望之,面面各成一势。舟行迅速,不能定取,不如以神存之,久则时入我笔端。此犀尖透月之理,断非粉本可传也。”能够简明扼要地在瞬间记录下物之“神”,是丰富的绘画经验、敏锐的体悟能力、高度的绘画技巧以及物象所特有的视觉冲击力和精神感召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要达到传神的地步,尤其一个画家进入一个陌生的地域,面对新奇的视觉感受,除了捕捉特有的“新鲜感”所蕴含的“传神”的某些因子外,还需要对物象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彻悟,真正把握其本质,而不被现象所迷惑。明代董其昌《画旨》所云:“画家以古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朝起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山行时见奇树,须四面取之。树有左看不入画,而右看入画者,前后亦尔。看得熟,自然传神。” 总之,写“真”、写“神”都是建立在物象“形质兼具”基础上的,是“形神兼备”的。 
三 写“趣”、写“妙” 在这里,“趣”与“妙”与中国传统美学意义上的“趣”与“妙”是有所区别的,是指自然界中那些“趣味横生”“神奇曼妙”的自然变化与画家心灵契合后的捕捉,包含对所视物象的气息气韵、动态的整体印象的捕获,对自然局部之奇之怪的特写,也包括在自然原型启发下“胸中臆气”的抒发。这种写生往往更加注重对自然独特性、瞬间性的直觉捕捉,情感宣泄的畅适性以及笔墨技巧甚至心理定式支配下(包括原有程式)的自由挥洒性。北宋《宣和画谱》卷十八载:“易元吉,……于是遂游于荆湖间,搜奇访古名山大川,每遇胜丽佳处,辄留其意,几与猿 鹿豕同游,故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毫端间,则是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也。”易元吉的画“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则是他“搜奇”“心传目击之妙”的结果。 米友仁自题《潇湘白云图》长卷中说:“夜雨欲霁,晓烟既泮,则其状类此,余盖戏为潇湘写千变万化不可名状神奇之趣……”后董其昌购得此卷,携以自随,“至洞庭舟次,斜阳篷底,一望空阔,长天云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戏也”。米友仁的“戏”为潇湘,则是对雨景变化神奇的捕获。 因此,这里的写生所指的“妙”“趣”,既包括对自然万物“妙”“趣”之景的把握、图式的把握、语言的把握,更涵盖其特有美感对画家精神的触动与升华。值得注意的是,写“趣”、写“妙”,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能力,并把这一想象迁入对象内部,从而写出把握其精神实质与自我心灵完美结合的“妙果”“趣果”。例如现代画家齐白石《江上所见》《余霞岭》等趣味盎然的妙品便是例证。 
四 写“意”、写“心” 写“意”、写“心”,是一种高级层面的写生,当画家面对自然物象时,不拘泥于其客体形貌,而是注重其神、势、气、韵的捕捉。他把自然界最最触动画家的绘画元素与画家的审美情趣进行了快速而有机的结合,自然对画家而言只是一个原型启发。在对自然景色进行主观取舍、提炼、组织、加工的过程中,既可以进行形式上的高度概括,也可以进行造型造景上的自由移位、嫁接甚至臆造。 总之,在写生中已经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想法、情感、感受和审美追求,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写生方法往往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画家为之,由于他已经形成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艺术语言、娴熟的表现技巧以及对自然敏锐的感悟力、对不同美感的迅捷捕捉力和转换力,因此,此写生则是画家心象的物化。黄宾虹说:“名画大家,师古人尤贵师造化,纯从真山水面目中写出性灵,不落寻常蹊径,是为极品。”例如,齐白石、黄宾虹,包括现当代很多画家的不少写生作品多属于这一类,在此不再赘述。 五 写“理” 写“理”,既可以明“物象之源”,把握物象之本,更是在面对自然、体验自然的过程中,升华到对人生、宇宙的感悟,进而写生出富有象征意义与精神内涵的意象,直接化为创作或为创作搭建桥梁。正如五代荆浩《笔法记》所说:“子既好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为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君子之德风也……其有楸、桐、椿、栎、榆、柳、桑、槐,形质皆异,其如远思即合,一一分明也。”11这主要说的是洞悉物象的精神之理。“山水之象,气势相生。故尖曰峰,平曰顶……夫画山水,无此象亦非也。”12这讲的是物象的自然之理。还有生活中看得见的“常理”,艺术中隐形的“艺理”等等,比如荆浩所说的“有形病”与“无形病”13便是。 写“理”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物象的生长体征、结构、肌理,以及物象之间的穿插、掩映等气势、脉络关系的“有形”之理的深刻把握,二是对写生物象“气”“韵”“神”等“无形”之理的准确把握。这既要画者有较高的对自然神韵的体悟能力,更要求画者“技近乎道”。建立在如此基础上的写生,才能细致入微,妙合自然,入其化境。 写“理”,不仅仅局限于探求物象、表现自然之理和气韵之理,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人生顿悟和哲理思考,即把天地万象作为表达自己理念的一种媒介。画家往往把这一介质进行人格化和象征性表达,通过高度概括、提炼,甚至抽象化的处理,达到其目的。《林泉高致》中把“大山”喻为“大君”,“长松”喻为“君子”,则作了如是观照。当代山水画家贾又福,几十次对太行山的深刻体验与写生,对其后来大量的“哲理与宇宙山水”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卢禹舜《静观八荒》系列等作品亦是在写生感悟基础上升华而成的。 
以上各种写生模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参用的。只是不同层次的写生者因侧重点相异而分别采用之。既可通过“对景写生”,也可采用“目识心记”的方式获得。 注:图文来自网上,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网站首页 > 文化 > 正文
网站首页 > 文化 > 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