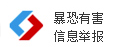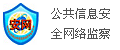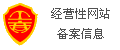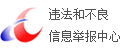|
提要:在推翻新法的政策诉求之外,司马光在政治上追求协调新旧关系,实现政治和解,重返多元政治。然而,他以做谏官的姿态做宰相,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既乏手段,又乏资源。相对年轻的台谏官群体主张清算,反对和解。新晋宰执推动太皇太后发布“务全大体诏”,对熙丰官僚实行政治赦免,力求和解。在台谏官强烈反对下,诏虽出而和解之义亡。元祐之政因而失去了大部分普通官僚的支持,进一步陷入“人才实难”的境地,而司马光对于变神宗法度的核心理论解释“干父之蛊说”被“以母改子说”掩盖,既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又为未来的分裂、恶斗埋下了引子。和解的破灭,司马光难辞其咎,然亦无法独任其责。 
一、问题的提出 统治集团的分裂、党争与政治清洗构成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源头可上溯至王安石—神宗对“异见”“流俗”的排斥打击。然而,当神宗驾崩之初,仍然存在着新旧兼用共改熙丰法度,避免进一步分裂、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这种对于政治和解的追求,宋人称之为“调停”。 开封陷落,宋室迁播,痛定思痛,宋高宗明确宣判了“调停”在政治上的不正确。因此,南宋人往往责备元祐君子除恶不尽,“调停”被视为导致了亡国惨剧的重大失误。在这种认识支配下,李焘才会为司马光辩护,力图把“元祐纯臣”司马光与“调停”切割开来。其实,不止是范纯仁、吕大防主张“调停”,司马光同样也主张新旧并用,力求和解。这一点,朱熹看得很明白,其批评司马光对王安石身后哀荣的处理过于宽大,又批评他用人没有严格区分是非邪正。其实,这正是司马光追求和解的表现。朱熹的观点带有强烈的时代偏见,而对“温公留章子厚,欲与之共变新法”的观察却是敏锐的。 和解最终并未实现,宋朝政治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分裂。和解破灭,原因何在?司马光难辞其咎。从表面上看,“似乎司马光走上了王安石的老路:执拗、听不进不同意见”。登上相位的司马光急不可耐、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最终有破坏而无建设。18个月的执政对政治造成了负面影响:保守主义黯然退场,北宋前中期士大夫政治中宽容异见的传统遭到进一步破坏,嘉祐成为遥远的绝响,皇帝—宰相的专制继续加强,士大夫集团内部的分裂加剧,党同伐异的政治气氛持续酝酿,直至哲宗亲政之后,出现了明目张胆的政治清洗,而司马光则因其最后18个月的政治行为,要对此负起主要责任。那么,司马光真背离了此前一以贯之的司马光吗?司马光能否承担起使和解破灭的主要责任?司马光与和解破灭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关于冀小斌所言的“司马光背离了司马光”,方诚峰的《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方诚峰以役法、对西夏关系为例,简单梳理了司马光在决策过程中的表现和作用,得出如下结论:“在重要事务上,司马光的主张不过是多种意见中的一种”,“司马光主政期间,在多数重要政事上,都做到了各种意见的并存”。而这种状况,方诚峰认为是司马光的主动追求。按照方诚峰的总结,司马光认为,要“避免本朝衰落”,就必须具备三大要素:“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才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沿着方诚峰的思路,甚至可以解答司马光何以“不许(苏)轼尽言”,在政策问题上表现出不通商量与固执己见:司马光主张多元意见,他的“己见”只是多元中的一元;而司马光自己当然认为“己见”是正确的,作为个体,他没有理由不坚持。按照理想状态,司马光的“己见”与各种“异见”平等竞争,构成多元意见共存的政治生态,具有判断力的理想君主兼听明断,择善而从。然而,这种理想状态与现实之间何啻南辕北辙:司马光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威望之重,都增重了他的“己见”,“己见”与“异见”之间本来就已经很难做到平等竞争;在垂帘体制之下,代行君主职责的太皇太后本身不具备完全的政治判断力,她依赖、信任司马光,以司马光的意见为意见;因此,“己见”与“异见”的平等竞争根本无法实现。最后,在多元意见之上,是司马光在“裁决其是非”,其最终之结果,必然是惟司马光之“己见”是从是执——主张多元并存的司马光最终也像王安石一样走向了一元。 历史事实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结果,过程中曾经无比丰富的可能性,最终却呈现为无法改变的唯一结果,研究者希望揭示的是从多种可能性走向唯一结果的过程。决定过程的是相关各方的选择与互动。在神、哲之际的政治过程中,“相关各方”主要包括太皇太后、宰执中的熙丰旧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新晋宰执、台谏官员,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各类“有司”中的普通官员,特别是中央的六部、地方的监司与州长,而司马光只是“相关各方”的其中之一。王夫之的批评、冀小斌的感叹,甚至方诚峰的分析,有着共同的默认前提,那便是此期的司马光,由于摄政的太皇太后的高度信任,掌握着朝廷的政治走向,是路线的总设计师和主要决策人,具有近乎决定一切的力量。如果他愿意,可以推翻新法、固执己见,也可以鼓励多元意见。这一政治形象的塑造,得力于苏轼的生花妙笔,但这一默认前提究竟是否真实?换言之,司马光在此期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 二、孤独的领袖:司马光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品格 按苏轼描述,司马光是在“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的强烈呼声下,顶着“反对派领袖”的光环重返政坛的。若以政治领袖的标准衡量,司马光的很多做法都令人费解。 第一,他与同为新晋宰执的吕公著、范纯仁之间缺乏必要沟通,更何况又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第二,对于宰执中的熙丰旧人,这些后世公认的司马光的政敌,司马光没有明确的排斥行为。相反,公开承认蔡确、韩缜、章惇等人的顾命之功。第三,新提拔的台谏官员,与司马光之间也不尽同调。司马光处理与上述三方关系的方式显然不符合后世对那个时代的解读。对政治同盟,他缺乏必要沟通;对政治上的敌人,他缺乏应有的警惕;应当倚为臂助的台谏官,他推荐的人选在政治上却并未与他保持一致。应怎样解释司马光的行为? 这一切都是司马光主动的政治选择,而他的政治选择则反映了他的政治品格。司马光在政策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神宗的新法,而在政治风气上则是希望重返多元宽容。在元丰五年的《遗表》当中,有司马光政改方案最简要的表达,包括政策调整与政风治理,而政风治理的重要性不下于政策调整。政治风气,即“风俗”。司马光对风俗的认识受到庞籍的影响,主要观点是风俗关系秩序的稳定,进而影响国家兴亡,风俗上行下效,靠在上之人的引导。对熙丰以来的“风俗”之弊,司马光痛心疾首。因此,司马光给太皇太后的第一个政治建议就是开言路,藉以端正政治风气。司马光衡量判断人与事的标准是是非,而非新旧、彼我。所以,在人事上,他既不刻意排斥熙丰旧人,也不刻意拉拢元祐新晋。 这种政治选择符合司马光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他是以做谏官的姿态做宰相,有意识地保持着个人的孤立。出任宰执之后,司马光在自家厅堂里贴了一张“客位榜”。然而,在这个时候贴出“客位榜”,声明所有与公务有关者都必须通过官方渠道上达,极有可能挫伤那些在熙丰时期受到排斥打击官员的积极性。可司马光却宁可冒此风险,也要维护个人形象的无私与国家制度的公正,这一方面反应了他的自律精神;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司马光毫无集合熙丰怨气以为己用的企图;他重返政坛的目的单纯,就是革除弊政,修复政风。与此相关联的是司马光在推荐人才方面的动作迟缓和保守。同为新晋宰执,吕公著态度积极,动作迅速。而司马光则是在太皇太后降下御前札子催促之后,才提供了一个21人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司马光声明:只有6人是“臣素所熟知”者;其余15人“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臣虽与往还不熟,不敢隐蔽”。这个名单表明“司马光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标准加于他所看重的臣僚”,它符合司马光诚实不欺、相对保守的一贯作风。 上述种种正暴露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致命弱点——缺乏政治斗争的实践经验,把政治简单化和理想化。他不要同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计,梦想靠着高尚的道德、严格的自律来感化、影响其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一厢情愿充分暴露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幼稚。 关于最后岁月的司马光,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内心感受。在15年闲居之后重返政坛,司马光义无反顾,坚信“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也说过“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来宣示自己的信心,然而在内心深处却不无忧惧,用“黄叶在烈风中”的“危坠感”来比喻自己的处境。隐藏在“危坠”感背后的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15年的疏离已经造成了司马光对开封政情、人事的高度隔膜。自王安石变法以来,朝廷的各项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司马光对新法只有耳闻目睹的印象,没有深入其中的经历和了解,制度不熟,人亦陌生。换句话说,司马光所能依靠的人才是相当有限的,他没什么“自己人”。 我们可以为生命最后时光的司马光画一幅简单的素描:体弱多病,内心充满忧惧,孤独地挺立在熙丰旧臣与元祐新晋之间,与双方都保持距离,一方面要推翻全部新法,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官僚集团的团结,目标明确,立场坚定,对于政治斗争复杂性既缺乏经验又不屑一顾。朝野上下无数人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熙丰失意人奉他为领袖,而这个领袖却没有自己的队伍。一言以蔽之,司马光是孤独的领袖。这样一个孤独的领袖怎么可能有能力主导如此复杂的政局? 三、太皇太后的权力实习与台谏官 在元祐政局走向加剧分裂的过程中,台谏官起了重要的推手作用,使台谏官得以发挥作用的是太皇太后的信任和依赖。这种信任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即是太皇太后学习掌控最高权力的过程,也是司马光对太皇太后的影响力相对衰减的过程。 从现存文字来看,元丰八年三月到六月,也就是司马光入相之前与初期,太皇太后与司马光之间,主要靠内侍往来传递信息。此类交流不可能全都落实在文字上,即便如此,《司马光集》还是透露了这种交流的频密程度。七月之后,司马光与太皇太后之间借助内侍的交流在现存文字中就不多见了。这种“不多见”,我以为应当代表着事实上的减少。原因不难猜度,一方面,司马光已经入相,双方有了制度化的定期见面机会。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司马光具有严格的自律精神,他更倾向于制度规范内的交流方式。 作为赵宋朝廷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太皇太后必须“速成”学习操控最高权力。元丰八年八月,太皇太后还在有意识地避免接见宰执以外的臣僚,包括台谏官。之所以这样选择,可能有藏拙的成分。她所能利用的学习渠道相对有限,主要包括宰执奏札、台谏官章疏以及与宰执、台谏的面对面交流。宰执之中,她所能信任的是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司马光则是她最信任的“导师”,而司马光也给了她持续不断的指导。台谏官是太皇太后的另一群“导师”。从记载来看,到元祐元年闰二月,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的接触开始变得密切起来,并逐渐形成相互配合的关系:台谏官提出意见、建议,太皇太后接受意见、建议,转而向宰执问责。太皇太后与台谏之间的沟通方式有两种:当面交谈与书面往复。太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在双日举行,隔日发生,频率极高,太皇太后又常常在单日接见台谏官,当面讨论问题。台谏官上殿,对所欲讨论的主要问题,通常写有札子,当面奏进;不及上殿,亦可专具奏札,随时进呈。对台谏官的书面上奏,太皇太后可以当面宣谕,亦可书面批示。书面往复与当面交流这两种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高密度的连续信息流,成为太皇太后了解、判断政治人物和形势的重要参考。 对熙丰弊政,苏辙也主张改,但他的任何更革主张都是假称“先帝本心”“先帝遗意”。兄弟同心,中书舍人苏轼草《吕惠卿贬建宁军节度副使制》,则用文字塑造了一个无辜的“先皇帝”形象。事实上,“彰先帝之失”,或者更准确的说“承认先帝有失”,对神宗之后的政局调整至关重要。惩处违法犯禁、罪行昭彰的个别官员与揪斗宰执级的大臣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前者作为清理官僚队伍的正常行为,可以得到理解和接受;而后者则极易引发整个官僚队伍的恐慌,并触发整个社会对于先帝的质疑。“先帝”有失,人所共知。不承认先帝之失,但却在先帝的时代揪出这样罪大恶极、祸国殃民的宰相大臣,只会引起思想混乱。 最聪明简便、不易引发混乱的做法是从先帝的言辞中找寻“悔咎”“欲改”的蛛丝马迹,从而把政策调整转换成“承先帝之志”的孝道行为。这样的努力,有人做了,比如殿中侍御史吕陶。司马光没有采取吕陶迂回的方式,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先帝有失。司马光的改先帝之过的理论,最为人熟知、遭人诟病的是“以母改子说”。其说出司马光于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献给太皇太后的《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然而细审文意,文章的核心绝非“以母改子”,而是“干父之蛊”。 司马光指出“天子之孝”不同于普通人的孝道,因此对先皇的做法要区别对待。《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蛊者,事有蛊弊而治之也。“干父之蛊”,“迹似相违,意则在于承继其业,成父之美也”。司马光还对“先帝之志”与实施结果进行了切割。到此为止,司马光完成了对“干父之蛊说”的构建,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区分了“天子之孝”与“庶民之孝”,“承父之业”与“承父之迹”,“先帝之志”与“先帝之治”,从而成功地证明“干父之蛊”、改革先帝弊政是一种孝道行为。文章到此,实际上已经完成。临到结尾,司马光又说:“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权同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这句画蛇添足的话所表达的是对太皇太后的鼓励;所流露的是司马光对于神宗的不满情绪。但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于经无据,于理不合。“以母改子”,将路线调整视为太皇太后与神宗母子之间的事情,将置小皇帝哲宗于何地哉!以儒学修养论,“以母改子”断非司马光之本意。 即便是“干父之蛊说”,司马光要皇帝来承担责任,承认先帝所为“有蛊弊”的理论,也不能为哲宗和主流所接受。元祐元年七月,年幼的哲宗在延和殿接见夏国使臣,使臣“辄妄奏曰:‘神宗自知错。’上起立变色,怒”。神宗如无过,何必改焉?神宗与王安石一脉相承,是思想上的父子,不能清算神宗便不能清算王安石,所能做也只是捉替罪羊,打落水狗。在生命的最后18个月,司马光被推上领袖高位,然而他既无人才队伍,也无经验、手腕、对策。历史赋予的任务一件也没有完成,这才是司马光最后18个月真正的悲剧性。 原载/《文史哲》2019年第5期,第24-40页;注释略
|


 网站首页 > 文化 > 正文
网站首页 > 文化 > 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