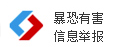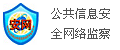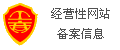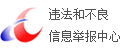|
(一)汉语是世界语言之祖? 备受争议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曾论证“汉语是印欧语系和世界其他语言的始祖母”;由于当时的学术界很西化,周先生的这一命题被批评和抵制,差不多成了绝响,是可想而知的。 但极为讽刺的,西方中心论之前的欧洲学者似有“先见之明”——17世纪的主流西方几乎共识:汉语是唯一的禀赋神性的“原初语言”,即纯正的“伊甸园语言”(被人类始祖使用的能够自由交流、普遍通感的语言);而相比之下,其余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各种语言,则是等而下之和支离破碎的“巴别塔语言”(被上帝打乱的、彼此隔阂的方言土语)。并且在17—18世纪的具体实践中,汉语成为欧洲各国的语言改革的向导和楷模;由此,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最显著的是英文——得以寄生于汉语,不仅幸免于难产或夭折,而且逐渐成熟和壮大起来。 更有甚者,在1760年代,英国人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1736 —1796年)按照类似于周有光的道理,利用汉语来“复活”古凯尔特语,他援引巴罗爵士的所言“汉语确实适用于发现凯尔特语的活的残留”;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参考别的中国资料,麦克弗森竟然虚构出《莪相》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古欧洲诗篇。它直接激发了催生德国文学的“狂飙突进运动”和伪造各国史诗的欧洲民粹狂潮,影响了好几代、成百上千的西方作家(首先是歌德和巴尔扎克)。 
图:汉语是世界的语言文字之母? (二)汉字是真正和完美的文字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和西化的误导,大家都以为汉字很落后,属于近似于原始的象形文字;而字母表音文字则为“高级文字”,有利于发展科学。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不是借助于汉字的“表意”,西方人根本不知道科学、文学和哲学为何物!仅从西方文字之“表音”特征来看,西方在文字上和其他方面皆无“原创基因”。 应该澄清文字的本质。“象形、表音、表意”是文字的不可分割的三要素,而单独的“象形”或“表音”则都是文字的缺陷或雏形。汉字是“形、音、义”之三位一体,兼容前两者,升华于“义”(表意)——它是超越性(形而上)的,因而能够做到“普遍共通”,此乃文字形成之必要前提。相比之下,生物性(形而下)的“象形”和“表音”所能表达的,分别是零星的视觉或个别的听觉;它们只能有助于狭小沟通,范围稍大便是障碍。 由于人的声音在空间上之差异、在时间上之变异,都是越来越大的;“表音”本身不能形成文字,否则的话,它就是自身难保——被声音的海洋所吞没。由此,西方的表音文字不能自体生成;除非它得力于外来因素,而得以畸形发展。 我们说西方的表音文字寄生于中国因素,那首先是因为:“表音”必须依靠:1.印刷术锁定和规范其符号(字母);2.便宜的纸张在交流中使该符号保持不变。若非如此,表音符号(字母)难免是信手涂鸦、乱成一团。 在使用印刷术之前,不可能存在表音文字。进而,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存在文字和文献。就像18世纪初的法国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所言:几乎全部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品和作家都是在14世纪后被伪造的。 (三)寄生于汉语的西方文字 倚靠四大发明而初起的西方(字母)表音文字远不成熟,备受挑战,生死未卜。在15—17世纪的欧洲,宗教文字(拉丁文等)和与此相对而出的世俗文字(方言文字)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冲突,以致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死人千万的宗教战争的症结。这是因为表音文字缺少“表意功能”(含义、定义),而使新文字徒增误解,火上浇油。 于是,从培根到莱布尼茨好几代的欧洲精英都以汉字为榜样致力于语言改革:虽然有不少人尝试设计类似于汉字的表意文字,但更多的和较成功的则是,利用“中国雅言”(汉语表意)来弥补西方表音文字的这一缺失。那就是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欧洲学者乘着“中国风、中国启蒙”(启蒙运动),使中国文化及其“雅言”(表意)融入他们的表音文字之中。这样,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也就能被用于抽象与形象的写作,从而变成了其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文字了。 拿英文来说,在莎士比亚生前(1564—1616年),英文尚不胜任于正规书写,直到在他死后大半个世纪仍是如此。所有的18世纪以前的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文本——特别是莎士比亚名下的作品,都主要由于其语言低劣的缘故,而在后来被改写或重写的。在17世纪的英国,培根、威尔金斯、斯威夫特和约翰·韦布等众多学者都倡导或进行“汉语模式”的语言改革;到ont FACE="Times New Roman">17世纪末乃初见成效,例如牛顿的写作从拉丁文改为英文。1755年《约翰逊英语词典》是英文臻于完善的标志,就像几位西方学者所揭示的:约翰逊博士是用汉语概念来定义英文的。 (四)“表意”之外没有原创文明 关于近代以前的西方实情,仅从文字学的视角来观察,便可“一叶知秋、一语中的”。“表音”意味着什么呢?它至少可以说明如下三点: 第一,西方无缘于原创文字,它也没有这种本事;因为在充满差异和变异的声音中来“表音”,怎么行?根本不会有代表性和共通性的!从“表音”来寻求文字,那是“死胡同、死脑筋”。所以说,若非幸遇外来文明,西方则无缘于文字。 第二,鉴于声音属于人的生理本能,如果社会交流模式仅限于“表音”,那就等于:除非其受变于外来文明,它恒为原始停滞,而无任何进步。实际上,西方正是如此:它在近代以前是“神本”,不存在“人为、人智”和“进步、进化”。 第三,没有文字,则无文献,也就不存在文明史。在其依靠中国因素产生了字母表音文字之后,西方伪造了“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另一方面,没有“表意”(形而上),也就不存在原创文学和哲学。 再来看象形文字。鉴于纯粹的或非表意的象形文字既是文字的雏形,又是文字的缺陷,它所能传达的只是具体的或零星的景象,而非整体的或系统的思想;因而,象形文字并不胜任于文明所需的交流媒介——原创文明应该是表意的,而非“象形”或“表音”的。据此,我们便可推断:拥有象形文字的“古埃及”、以及它的文明与历史,都是不存在的。两者是“双伪互证”,这是很容易被揭穿的。所谓的埃及象形文字仅有极小部分是原始文字,却被夸大了;而绝大部分则是被伪造的,冒充“古老文明”的文字。 “古埃及”是怎样出笼的呢?它是西方史学“三巨头”进行累进伪造的结果:1.臭名昭著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开拓“西方全史”:“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但缺乏时间概念;2.“编年史之父”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按照中国编年史及其计算方法,设计出“西方编年全史”,因而安尼乌斯的虚构被“扶正”;3.“埃及学之父”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使用中国资料补充“古埃及”的文明与文字,他也是编造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罪魁祸首。 FONT>“复制中国”。〔详见 诸玄识 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 
图:“埃及学之父”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他首先汇编出中国资料(中),再按照其中的内容来伪造“古埃及”文明和文字(象形文字)。 本文作者:诸玄识 董并生;编辑:郑文明
|


 网站首页 > 文化 > 正文
网站首页 > 文化 > 正文